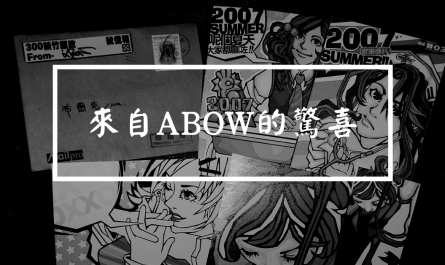媽媽啟程踏上通往天國的長途旅行了。這些年來,我始終記得當年 18 歲的自己,對爸爸許下的那句承諾──我會好好照顧媽媽。轉眼三十年過去,我已走到 48 歲的人生階段,這份承諾也在歲月裡沉甸甸地落地、生根。
媽媽最後的時光格外辛苦。她一口一口艱難的喘息,像用盡全身力氣與生命拔河;每一次急促的吸氣,都震得整張病床微微發抖,也震得我心裡一陣陣揪緊。這四天,她真的太辛苦了。
終於,在 12 月 4 日,她累了,也終於可以放下這世間所有的勞苦,不再被病痛糾纏。她的呼吸停在那一天,而她的安息,也讓我的心在惆悵中,生出一絲微微的釋然。
被拖著走的疾病,與來不及的心疼
去年,媽媽幾乎是工作到體力再也撐不住,才肯稍作休息。家庭代工的日子本就辛苦,收入微薄又缺乏保障,她總是硬撐著,把所有的疲憊吞進心裡。那天她回家時,就覺得右腳使不上力;我們都以為只是累了,誰也沒想到,那是一段漫長病痛旅程的開始。
隔幾天,媽媽在家中跌倒,竟然爬不起來。她就那樣孤單地躺在地上,好幾個小時,直到天黑了,才終於摸到手機,顫抖著打電話給我。那一刻,我才驚覺事情不對,心像被掐住般緊縮。
其實早就勸媽媽要去看醫生,但她依著自己的習慣,一直撐,硬是等到重陽節後,才願意就醫。10 月 11 日,她因為不明分泌物掛了婦科;隔天 10 月 12 日,又因右腳無力轉看神經內科。只是中風的跡象不算明顯,因此一延再延,時間就在這樣的忽略與心疼間悄悄溜走。
直到醫生看診後,臉色一變,立刻轉送急診。檢查、治療、焦慮的等待……卻因等不到病房,只能在 10 月 14 日再轉往台北榮總。那段時間,在亞東醫院往返時,媽媽已經需要依靠爬梯機上下樓梯。右半身中風後,右腳完全使不上力,只能靠左腳強撐著。最後,連左腳也支撐不住,疼得無法落地。
就這樣,在急診區待了五天,終於進入病房,展開治療,也開始復健。但一切的努力,都帶著深深的、來不及的酸楚。
在漫長的路上,一步一步重新學會走路
中風後的復健,是一條既漫長又孤獨的道路。10 月 16 日,媽媽從急診轉入神經內科病房,完成初步治療後,下一步便是尋找復健病房,讓康復能延續不間斷。然而復健病房一床難求,一度讓人擔心是否得在茫茫醫療體系中四處漂泊。感謝主,終於在 11 月 10 日順利從神經內科地轉到五樓的復健病房,媽媽得以繼續堅持這條艱辛的路。
只是,復健病房的停留僅有 28 天的限制,我也必須提前開始奔走下一個落腳處。雙和醫院、台北醫院、和平醫院、中興醫院、北護醫院……一間間詢問、登記排床,卻始終等不到一個確定的床位。終於到了 12 月 9 日出院時,仍然沒有接續的復健病房,只能先選擇回家,之後再至和平醫院門診方式繼續復健。
令人欣慰的是,在榮總的復健成效明顯。媽媽回到家後,竟能重新開始自己走路,也能緩慢地上下樓梯。每一次復健日,她都一步一腳印地走下樓梯,再搭計程車到和平醫院。那時她還能用敬老卡搭乘、扣抵點數─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,卻讓人覺得無比珍貴。因為,每一次能自己踏出的步伐,都是媽媽努力堅持生命的證據,是她與病痛對抗後的微光。
在復健與生活之間,努力尋找一條能同行的路
12 月 26 日,我帶著媽媽到和平醫院復健科門診,正式開始安排後續的復健行程。醫院替我們排定每週三、五的固定時段,雖然對她的治療很重要,卻多少會影響我的上班時間。於是,我撥打了 1922,詢問是否能申請長照的喘息服務,希望能有人協助陪同就醫。1 月 6 日,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寄來回函,並通知隔天──1 月 7 日,將由個管師前來評估長照等級。
在核准之前,所有的路程、等候與照顧仍然只能由我親自承擔。每一次復健後,我都會牽著媽媽,帶她到和平醫院附近找些能坐下來吃的、簡單卻溫暖的一餐。她不能走太遠,但我們依然努力在有限的生活圈裡,替她找些小小的「新鮮感」,像是用味蕾提醒生命:我們還在一起努力。
只是和平醫院的復健較著重在上半身,對她真正需要的幫助有限。我也在心裡反覆思考,是不是該再找另一種方式,讓她能更有力量地站起來。
沒想到 1 月 12 日,媽媽的右腳突然紅腫、刺痛,我心裡立刻浮現可能是蜂窩性組織炎的警訊,隨即送她到和平醫院急診。果然被留了下來打抗生素,同時等待病房。那幾天,她安靜地躺著,身體努力對抗感染;我則陪在旁邊,看著點滴一滴滴落下,心裡默默祈禱。
18 日,她終於出院,改以口服抗生素。之後的日子,我們又回到門診持續觀察,也繼續在復健的道路上,跌跌撞撞地往前走。每一步都辛苦,但每一步,我都希望能陪她一起。
原以為只是腫脹,卻沒想到是生命另一種苦痛的開始
出院後,媽媽恢復了復健,也按時回診。2 月 11 日回診時,醫生評估口服抗生素的效果不如預期,於是安排她在 2 月 14 日門診後再次住院。這一住,就是從 14 日到 27 日,漫長又沉重的兩週。
在和平醫院的治療期間,醫生逐漸察覺腳腫似乎不僅是蜂窩性組織炎那麼單純。進一步檢查後,醫生的表情變得凝重──他告訴我們,媽媽的狀況其實是「子宮體腫瘤併侵犯骨盆腔」,腫瘤壓迫了右側髂骨靜脈,加上右下肢淋巴水腫,使得感染遲遲無法改善。
這不是我們原本以為可以靠抗生素解決的問題,而是更深、更複雜的病灶。和平醫院的設備無法提供進一步的治療,因此醫生建議轉診到教學醫院,並立刻開了轉診單。
就在那一刻,我心裡浮起一陣冰冷的空洞——原來媽媽承受的痛,不只是腫脹與感染,而是一場更艱難、更未知的戰役。拿到轉診單後,我沒有時間沉浸在震驚裡,只能立刻開始尋找榮總婦科門診的掛號。因為媽媽的病,已經不容許我們多浪費一分一秒。
聽見診斷那天,時間彷彿在胸口慢慢碎裂
3 月 3 日,我先帶媽媽回神經腦血管科回診、拿藥,同時也掛了婦產科門診。醫師看過後,立即為她簽下住院單,再次安排住院治療蜂窩性組織炎,並進行更深入的檢查。3 月 7 日,她接受了切片檢查;所有檢查和治療告一段落後,3 月 11 日媽媽再一次出院。
但真正的風暴,是在 3 月 17 日的回診室裡揭開的。
醫生的診斷結果,是子宮內膜癌第四期。那瞬間,我的心像被風吹斷的枝丫,無聲、卻劇烈地折裂。醫師解釋,腫瘤太大,已向周邊組織擴散,加上媽媽肺部浸潤嚴重,如果進行長達一整天的手術,身體恐怕承受不了。因此不建議立即動刀,而是先以化療讓腫瘤縮小,再視情況進行後續手術。
明明是為了爭取生機的治療計畫,可那一刻,我卻只覺得世界變得遼闊而刺骨。醫生說完後,便安排隔天──3 月 18 日──讓媽媽住院接受化療。
那是我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:這段路,不再只是治療,而是一場與時間賽跑、與生命重量搏鬥的旅程。
在化療的艱路上,每一次堅強都藏著她未說出的痛
進入第一次化療後,媽媽先接受發炎指數的控制與身體調理,讓她能撐過第一次的療程。為了提高血紅素,我們幾乎把能補鐵的食物全都吃了一輪──豬血湯、牛肉湯、葡萄、蘋果……只要對她有幫助,我就想盡辦法準備。化療必須間隔 21 天一次,為了讓注射與抽血能更順利,媽媽同意置入人工血管,並於 4 月 10 日進行手術。這個決定並不容易,因為她的血管非常細、難以找到位置,每次抽血都要折騰很久,有時甚至需要整個病房的護理師一起幫忙。第一輪化療終於在 4 月 11 日結束,那天媽媽疲倦得連眼神都散成柔弱的光。
第二次化療在 4 月 21 日住院,一住就是到 5 月 16 日。其間的 5 月 12 日到 21 日,我因工作前往香港、澳門拜訪教會機構,只能請哥哥暫時接手照顧媽媽。回國後,我立即回到家中,再次接過照顧她的責任。按理化療住院只需要三天,但媽媽的發炎指數與血紅素常常不在理想範圍,治療前總得一再調整,把身體狀態拉回能承受的程度。化療後她的體力明顯下滑,反胃幾天後才能正常吃,但味覺逐漸改變,視力也慢慢變得模糊──那是化療在她身體裡留下的無聲戰場。
第三次化療在 6 月 2 日住院、6 月 5 日出院;第四次則是 6 月 24 日住院、6 月 28 日出院。這兩次相對平順,因為腫瘤開始縮小,讓後續治療有了些許希望。醫生因此安排 7 月 7 日住院,並於 7 月 9 日進行手術。
然而,媽媽肺浸潤嚴重,全身麻醉後是否能甦醒,是醫師與我們最深的擔憂。術後她直接被送入加護病房,一直到 7 月 13 日才轉回一般病房。因為血紅素低、呼吸不穩,她仍插著呼吸管與鼻胃管。這兩條管子讓她非常難受,她總是反覆寫著問我:「什麼時候可以拔掉?拔掉我就能說話了。」
那一刻,我多麼希望能回答她:「很快、真的很快。」但我知道,我只能握著她的手,替她承受那份焦急與委屈。
媽媽在病房慢慢調養,直到 7 月 23 日出院,回家修養,準備迎接術後的化療。
那是一段漫長而疲憊的路,她一步一步撐著;而我,也在她身旁,一次又一次地學會什麼叫「陪伴」。
化療之後,她的世界只剩下一口勉強入口的粥
術後媽媽的恢復情況原本良好,但右腳依舊持續腫脹。8 月 10 日,她再次住院進行第五次化療,直到 8 月 13 日才出院。只是,術後化療帶給身體的衝擊比之前更猛烈,她的體力與精神明顯快速下滑,食慾也一天天減退。
原本能吃的東西,到了口中都太乾、太硬、太難吞嚥,後來幾乎所有食物都改成粥。連醫院餐點,她也只吃粥和幾口菜,才勉強能吃下一些,偶而也會有胃口好的時候,把粥和菜都吃完。但只要腥味稍重,尤其海鮮類,她就會反胃得厲害。家裡的冰箱因此長期儲備著優格、甜湯、微波餐點;桌上也擺著豬肉乾、牛肉乾、餅乾等零嘴──只要媽媽突然想吃,我就希望她能立刻有東西能入口。
但隨著化療讓身體越來越虛弱,她連微波食物的味道也開始感到厭倦。那些曾經為她準備、希望能讓她補充體力的食物,在後來竟成了她疲乏與無力的象徵。
看著她從能吃、願意吃,到最後只能挑著勉強入口的東西,我心裡的酸楚,比任何苦味都更難吞嚥。
照顧的路上,我一邊撐著她,一邊責怪著自己
第六次化療在 8 月 31 日住院,9 月 2 日出院後,我便與居服員於 9 月 4 日簽約,重新調整照護方式──每週兩天代購午餐,一天協助洗澡,其餘時間依然由我自行準備。每天早晚餐,我盡可能變化、搭配,偶爾以微波食物交替,只希望她願意多吃一點、多留住一點體力。
第七次化療在 9 月 21 日住院、9 月 23 日出院;第八次則是 10 月 12 日住院、10 月 15 日出院。但這次出院後,媽媽的身體狀況明顯急遽下滑。偏偏在這次住院期間因為請不到看護,我必須通宵陪護一晚。隔天回家便開始咳嗽、出現感冒症狀,我立刻去看醫生,但身為同住照顧者,無論多小心,仍難以完全避免彼此感染。
果然,媽媽也開始發燒、咳得更厲害。我心裡的內疚像潮水般不斷湧上來──明明她的身體那麼脆弱,化療已把她折磨得不剩多少力氣,而我竟還把病帶給她。
我問她要不要去急診,她卻堅定地搖頭。 她說:「我住院住到煩了,不想再去了。先吃成藥、退燒藥就好。」
我知道這樣並不好,但看著她反覆住院已經疲累不堪,我只能尊重她的選擇。
可是在尊重之下,我的心卻揪得更緊。我一遍遍責怪自己──怎麼沒有把自己照顧好?怎麼會讓她在最虛弱的時候承受來自我的感染?
照顧者最深的無力,大概不是身體的疲憊,而是明明已經拼盡全力,卻依然覺得「做得不夠」。
在最後的化療裡,她用盡力氣,而我用盡心痛
最後一次化療住院是在 11 月 2 日。剛入院量體溫就微微發燒,醫生評估後認為雖然狀況還算穩定,但因發炎指數偏高,仍決定先以抗生素治療。起初似乎有效,可沒過多久,發炎指數再度急速攀升,只能再換一種抗生素繼續治療。就這樣,一天又一天,兩週悄悄地熬了過去。
除了發燒外,媽媽的右腳又因為血栓而脹痛,她得接受抗生素治療,同時還需要注射溶血栓劑與口服藥物。
住院前幾天,媽媽還能勉強吃點東西,但後來卻是吃什麼吐什麼,連藥也無法順利吞下。醫師問是否要放置鼻胃管餵食,但媽媽堅決不要。我尊重她的意願,只是看著她因無法進食而日漸消瘦,心裡疼得像被撕開。
她說,自己的身體像進入一個殘忍的循環:好一點,又更差。兩週的禁食,僅靠營養液支撐,精神狀況每天都在下滑。咳嗽不斷,吃藥後也常常立刻吐出來。到了後期,她竟因飢餓而出現幻覺,會告訴我她正在吃蔥油餅、正在喝蛤蠣湯、正在吃蘋果、吃蝦子。每當她描述那些「不存在的食物」時,我的眼眶就會發熱──因為那些,是她的身體最誠實的呼喊。
與醫生討論後,我們嘗試恢復少量進食。但媽媽的睡眠越來越差,夜裡常自言自語,甚至影響隔壁的病床。她有次對我說:「都沒有人跟我說話。」那句話像一把鈍刀,慢慢割進心裡。看她的 YouTube 觀看紀錄停在 11 月 4 日,我才意識到,她已經無力再做平常會做的事。
這次住院,她承受的辛苦與無助,是過去所有住院中最沉重的一次。
11 月 28 日,媽媽在上廁所時腿軟跌倒,看護拉不住她,頭撞出一個腫包,也留下瘀血。幸好檢查後沒有大礙。為了避免再度跌倒,醫護團隊決定讓她暫時不要下床,並插了尿管。
那時的她,已經虛弱到連站都站不穩。而我,則在一旁無力地看著──
看著她一寸寸被病痛奪去力氣,
看著她在最後的化療裡,用盡全部的韌性與勇氣,
而我能做的,只剩握住她的手,陪她走向生命最後這段最艱難的路。
當世界逐漸暗淡,她的生活只剩下一種難以言說的辛酸
對媽媽而言,自從中風後不能自由走動,心情早已蒙上一層陰影;更別提在住院期間,常常沒有可以聊天的人。視力模糊到看不清手機,看劇也只是聽著聲音在耳邊飄過,所有讓她打發時間的小樂趣,彷彿都在一點一滴地離她而去。
吃東西更是一種折磨。她過去喜歡的食物,如今入口都是苦味;稍微味道重一點,就容易反胃。最初還能靠著「好吃的」多吃幾口,後來卻變成吃什麼吐什麼,連吞咽都成了負擔。
看著她這樣,我心裡那種無力與心酸,很難用語言形容。不是因為她喊痛、喊苦,而是她已經連抱怨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她只是安靜地承受著──
而我只能在旁邊看著,感覺自己什麼都做不了。
那份心疼,是悄悄往內沉、卻揮不走的。
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裡,我陪著她走完最漫長的一段路
11 月 30 日早上,醫院打來說媽媽血氧下降、狀況不佳,要我立刻前往。到院後,我簽下病危通知,同時也簽署放棄急救、放棄插管與強心針等同意書。只是這些文件需要第二位家屬見證,哥哥尚未從斯里蘭卡回來,只能等他返國後 12 月 1 日再補簽。醫師詢問是否同意使用嗎啡──它能讓呼吸舒服一些,但也可能抑制呼吸。那一刻,我心裡只有一個想法:
最後的路,讓媽媽舒服,就是我們能給的最好選擇。
看護提醒需要準備看護墊與紙尿布,當晚我又回醫院一趟。媽媽那時精神依舊不好,整個人像在虛弱的迷霧裡漂浮。
12 月 1 日,媽媽的兄弟姐妹來探望她。晚上我與哥哥再度前往醫院,完成了第二位見證人的簽署。那天媽媽睜開眼,看著我說了一句:「辛苦你了。」
那聲音輕得像風,但卻讓我心碎得難以承受。
那夜我們帶著不捨離開病房。哥哥則先在家住一晚,隔天再到醫院陪伴。
12 月 2 日一早,醫生又來電──媽媽血氧降到 70,怎麼調也上不來,已經使用最後階段的非侵入性供氧面罩,請家屬儘速到院。
我趕到後,看見媽媽仍在昏睡中,生命跡象雖弱但穩定。小阿姨、二姊陸續前來探望。傍晚以琳送餐來慰問,也進房看了媽媽一眼,那時媽媽還曾睜開眼,看了看我們。
討論過後,我讓看護先行下班,由我和哥哥輪守。那一晚,她算是安穩地睡著。
只是,我與哥哥一路照顧媽媽,都沒把自己的藥帶在身上。又因不確定媽媽何時會走,兩人不敢同時離開。最後決定輪流回家換洗、拿藥。
3 日下午,我先回家一趟,晚上再換哥哥回新竹取藥。隔天一早,他便趕回醫院。
到了 12 月 4 日早上,媽媽的血氧從原本勉強維持在 80,再度下滑到 70,血壓也持續下降。我們依舊照著護理指示,每兩小時為她翻身。
接近 11 點時,翻身並抽痰後,媽媽的狀況急轉直下。心跳與血壓同時往下落。我看著她,眼角滑下一痕淚。
我再也忍不住,替她擦去那滴眼淚──
那不是痛苦的眼淚,而像是她要對我們說的最後一句話:
「孩子,我要走了。」
就在那樣安靜的一刻,她的心跳停了。
12 月 4 日,那天媽媽「出院」了。
這一次,不再是轉院,不再是準備下一次住院,而是──
她終於畢業了,離開了這些病痛折磨的日子。
而我,也在她生命最後的一刻,握著她的手,送她走完這條漫長又心碎的旅程。
遺憾無法抹去,但愛與努力從未缺席
是否有留下遺憾呢?
媽媽有沒有?
我不知道。
但對我而言──一定有。只是我也確信,在那些有限的時間、有限的能力、有限的選擇裡,我真的已經盡力了。
現實生活裡,很多事情本就充滿無奈。冷凍庫還塞滿著媽媽喜歡的鮭魚、白帶魚──那些我特地買給她、卻來不及讓她嘗一口的食物。每次打開冰箱,看著那些未被吃過的味道,都會讓我胸口悶起一陣惆悵:
原來遺憾,有時只是靜靜躺在冷凍室的一個角落。
我不是一個喜歡賺錢的人。過去扛著家裡的債務,還得很慢、很辛苦,眼看明年就要全部還清,本以為終於能比較沒有壓力,能帶媽媽出去走走。她常笑說自己是路痴,需要有人帶著她,而我也期待著等財務終於鬆一口氣時,可以牽著她的手去看看世界。
但現實卻沒留給我們那個機會。
這些年,我把時間都埋在工作裡,不是因為想賺更多,而是工作就不會外出、不會花錢,能省就省。只可惜,這樣的省,也省掉了與媽媽許多美好相伴的時光。帶她出去走走的願望,最終只停留在想像中。真正做到的,只是帶她在家附近吃喝小確幸而已。
住院後,我每天報到;回家時就想著多煮點東西給她吃。媽媽以前常說很久沒吃過我煮的東西,而過去這一年裡,她的早餐幾乎全是我親手準備的。這是我晚來的彌補,也是我能為她做的最溫柔的日常。
《韓詩外傳》說:「樹欲靜而風不止,子欲養而親不待也。」
我如今才真正明白這句話的重量。
我們之間也曾因金錢觀念而爭執,我不希望把賺來的錢都交給金融體系,卻換不到半點生活品質。看著保險、貸款、信用卡利息一路吞噬過去的歲月,那些都是壓在我身上的負擔,而我也只能默默扛下來。這些,是我對媽媽的小小抱怨,也是一段屬於我們彼此之間的生活痕跡。
如今,一切都過去了。
錢,只要夠用就好了。
媽媽,也已經放下所有勞苦。
剩下要整理的是我自己。
未來的日子還在繼續,可回歸日常卻異常安靜。心裡的難過與感傷沒有出口,也不知道要向誰說、該怎麼說。那些情感寄託,一夕之間像被抽空,只剩下夜裡的淚水陪著我慢慢睡去。
這幾晚我幾乎都是哭著入睡。
哭完以為會比較好,可醒來時仍是一身沈重。
日子還是會往前走,只是我不知道──
何時我才能真正息下這世上的勞苦與愁煩。
但至少,在媽媽最需要的時候,我一直都在。
而這份陪伴,就是愛。
是無法抹去遺憾,但也足以溫暖遺憾的愛。